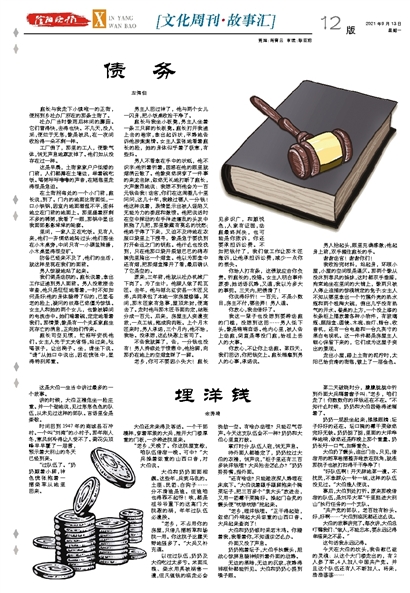余秀琦
这是大伯一生当中讲过最多的一个故事。
讲的时候,大伯正襟危坐一脸庄重。并一个劲地说,见过形形色色的队伍,从未见过这样的部队。言语里全是崇敬。
时间回到1947年的商城县石冲村。一个叫“刘湾”的小村子。那年刚入冬,寒风刮冷得让人受不了。菊花尖顶峰早早覆了一层雪,预示着大别山的冬天已经到来。
“过队伍了。”奶奶颠着小脚,神色慌张抱着一捆柴草从地里回来。
大伯还未来得及答话。一个干部模样,穿着军装的大兵,推开大门楼厚重的门板,一步跨进院里来。
“老乡,天晚了。你这院屋宽敞,咱队伍借宿一晚。可中?”大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大伯说。
大伯和奶奶面面相觑。这些年,兵荒马乱的。土匪、民团、白狗子……分不清谁是谁。但谁咱也得罪不起呀!唉,都是祖爷爷置下的这高门大院惹的祸,年年过队伍必遭殃。
“老乡,不占用你的房屋,只借几捆稻草和场院一用。你这院子比露天野地强多了。”大兵又补充道。
以往过队伍,奶奶及大伯吃过太多亏。米面瓜粮、柴水用具被祸害一遭,但凡值钱的临走必会洗劫一空。有啥办法哩?只能忍气吞声。今天这支队伍会不一样?奶奶和大伯心里直打鼓。
掌灯时分,队伍入驻,悄无声息。
待外面人都睡定了,奶奶拉过大伯的衣襟,悄声说,“柜子里还有三百多块洋钱哩?大兵抢去怎么办?”奶奶努努嘴,指外面。
“还有啥法?只能趁夜深人静埋在床底下。”大伯说着蹑手蹑脚抱来个腌菜坛子,把三百多个“袁大头”放进去,又用一团霉干菜腌好。操起门旮旯的镢头便“吭哧吭哧”挖起来。
“老乡,埋洋钱哩。”正干得起劲,忽然门外响起大兵浓重的山西口音。大兵起来查岗了!
大伯和奶奶顿时呆若木鸡。你瞪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外面又没了声息。
奶奶抱着坛子,大伯手执镢头,胆战心惊屏息凝神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无边的黑暗,无边的沉寂,夜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大伯和奶奶心提到嗓子眼。
第二天破晓时分,朦朦胧胧中听到外面大兵隔着窗子叫:“老乡,咱们走了!你数数你的洋钱还在不在。”不知什么时候,奶奶和大伯困倦得迷糊着了。
奶奶一屁股坐起来,揉揉眼睛:坛子好好的还在。坛口腌的霉干菜依然完好无缺。奶奶掂了掂,里面的大洋哗哗地响,依然还是昨晚上那个重量。奶奶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
大伯扔了镢头,追出门去。只见,借宿用的稻草卷捆整齐堆放在院角,就连那院子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好队伍啊!开天辟地第一遭。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样的队伍没见过。”大伯逢人便说。
事后,大伯到处打听。原来那晚借宿的队伍,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执行任务的一个支队。
“共产党的部队,老百姓有盼头。好,好啊……”大伯到临死都还这么说。
大伯的故事讲完了。每次讲,大伯总叮嘱我们:“做人,不能忘本,要永远记得幸福来之不易。”
这句话我永远记得。
今天在大伯的坟头,我告慰已逝的灵魂:从这个大门楼走出的,有2人参了军,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这个队伍还有人不断加入。将来,浩浩荡荡……
温馨提示
本页面内容不允许直接阅读,请通过《信阳日报》客户端浏览查看。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