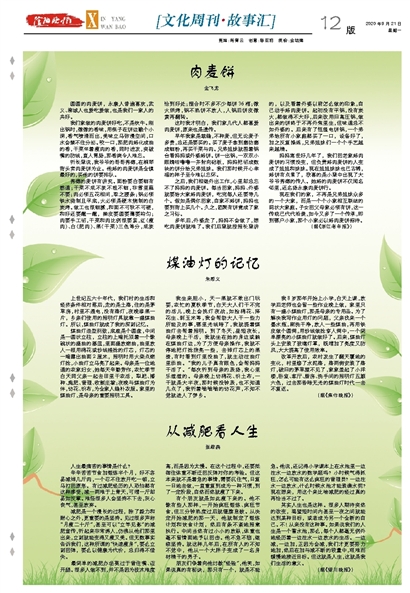朱帮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的生活和经济条件相对落后,走的是土路,住的是茅草房,村里不通电,没有路灯,夜晚漆黑一片,乡亲们使用的照明灯具就靠一盏煤油灯。所以,煤油灯就成了我的深刻记忆。
煤油灯造型别致,底座是个圆盘,中间是一圆状立柱,立柱的上端托顶着一个像碗状的盛油的器皿,里面盛放燃油,油里放入一根用棉花或纱线搓捻的灯芯,灯芯的一端露出油面2厘米,照明时用火柴点燃灯捻,小油灯立马亮了起来。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家妇女,她每天辛勤劳作,农忙季节白天同父亲一起去田里干农活,犁耙、播种、施肥、管理、收割庄稼;夜晚与煤油灯为伴,纺花、织布,为全家人缝补衣服。家里的煤油灯,是母亲的重要照明工具。
我生来胆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玩耍,农忙的夏秋季节,白天大人们干不完的活儿,晚上会挑灯夜战,如捡棉花、择花生、剥玉米等,我会帮助大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哪里光线暗了,我就提着煤油灯去帮着照明。到了冬天,昼短夜长,母亲晚上干活,我就坐在她的身边或躺在煤油灯边,为了方便母亲操作,我就不停地把灯捻拨亮一些,去掉灯芯上的黑渣,有时看到灯里没油了,就主动往油灯里添油。“我的儿子真有眼色,会帮妈妈干活了。”每次听到母亲的表扬,我心里乐滋滋的。母亲晚上纺棉花、织土布,一干就是大半夜,那时候没钟表,也不知道几点了,我听着嗡嗡嗡的纺花声,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我8岁那年开始上小学,白天上课,放学后老师也会留一些作业晚上做,家里只有一盏小煤油灯,那是母亲的专用品。为了解决我写作业用灯的问题,父亲找来一个墨水瓶,刷洗干净,放入一些煤油,再用铁皮做个圆筒,用纱线做捻穿入筒中,一个简单漂亮的小煤油灯就做好了。后来,煤油灯头上安装了玻璃灯罩,既增加了亮度又防风,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修了水泥路,路两侧安装了路灯,破旧的茅草屋不见了,家家盖起了小洋楼,卧室、客厅、厨房、洗手间的照明灯五颜六色,过去那昏暗无光的煤油灯时代一去不复返。
(据《焦作晚报》)
温馨提示
本页面内容不允许直接阅读,请通过《信阳日报》客户端浏览查看。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