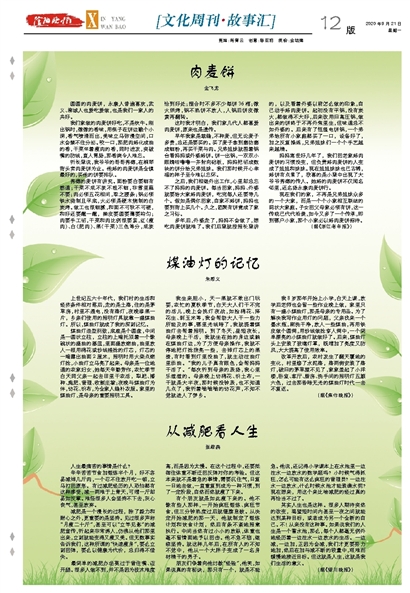金飞龙
圆圆的肉麦饼,永康人普遍喜欢,武义、柳城人也爱吃爱做,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好。
我们家做的肉麦饼好吃,不是吹牛。刚出锅时,微微的香味,用筷子在饼边戳个小洞,香气喷涌而出,美味立马弥漫空间,口水会禁不住分泌。咬一口,那肥肉烙化成油的香,干菜裏着瘦肉的香,同时迸发,突破嘴的防线,直入胃肠,那香爽令人难忘。
听长辈说,我爷爷的哥哥秀德,在桐琴街头卖肉麦饼为业。他烙的肉麦饼是全镇最好的,买他的饼要排队。
秀德的麦饼有讲究。面粉要白要细有筋道;干菜不咸不淡不粗不细,非雪里蕻不要;肉必须五花相间,取之腰条;锅必须铁水浇制且平底,火必须是硬木烧制的白炭烤。做工也很细腻,和面不可软不可硬,和好还要醒一醒,擀皮要圆要薄要均匀;肉要手工切,干菜和肉比例很要紧,红(瘦肉)、白(肥肉)、黑(干菜)三色等分,咸淡恰到好处;捏合时不多不少每饼36褶;微火烘烤,锅不热饼不放入,入锅后饼皮微黄再翻转。
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家几代人都喜爱肉麦饼,原来也是遗传。
早年我家是裁缝,不种麦,但无论麦子多贵,总还是要买的。买了麦子拿到磨坊磨成细粉,再买干菜与肉。兄弟姐妹就围着锅台看妈妈或外婆烙饼。饼一出锅,一双双小眼睛咕噜噜一齐射向砧板,妈妈把切成数块的饼分给兄弟姐妹。我们那时候开心幸福的样子至今难以忘怀。
之后,我们相继外出工作,心里却总忘不了妈妈的肉麦饼。每当回家,妈妈、外婆就要给大家烙肉麦饼,吃完每人还要带几个。假如是偶尔回家,自家不烙饼,妈妈也要到街上买几个。久之,团聚有饼竟成了家之习俗。
多年后,外婆走了,妈妈不会做了,想吃肉麦饼就难了。我们后辈就按照长辈讲的,以及看着外婆以前怎么做的印象,自己动手烙肉麦饼。起初没有平锅,没有炭火,都做得不大好,后来改用旧高压锅,做出来的饼终于不再外焦里生,但味道总不如外婆的。后来有了恒温电饼锅,一个弟弟给所有小家庭都买了一口,设备好了,加之反复操练,兄弟姐妹们一个个手艺越来越精。
妈妈离世好几年了,我们回老家烙肉麦饼的习惯没变,但负责烙肉麦饼的人变成了姐姐和妹妹。现在姐姐妹妹也已古稀,烙饼有点累了,欣喜的是小辈中出现了大爷爷秀德的传人。她烙的肉麦饼不仅闻名邻里,还名扬永康肉麦饼行。
现在我们的家,不再是兄弟姐妹众多的一个大家,而是一个个小家相互联结的网状大家庭。子女回父母家必须有饼,这一传统已代代沿袭,如今又多了一个传承,即到哪户小家,那个小家必以烙肉麦饼招待。
(据《浙江老年报》)
温馨提示
本页面内容不允许直接阅读,请通过《信阳日报》客户端浏览查看。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