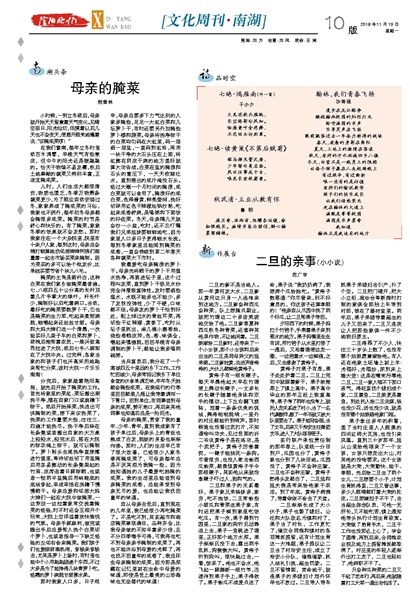殷雪林
小时候,一到立冬前后,母亲就开始天天留意着天气变化。见晴空丽日、阳光灿烂,估摸着以后几天也不会变天,便眉开眼笑地嚷着说:“该腌咸菜!”
在我们豫南,每年立冬时虽然百木凋零,早晚天气有些寒凉,但中午的阳光还是暖融融的。恰天干物燥不易发霉,秋后土地奉献的蔬菜又特别丰富,正适宜腌咸菜。
儿时,人们生活大都很清贫,物质也匮乏,冬季万物萧条蔬菜更少,为了顺应自然安稳过冬,家家养成了腌咸菜的习俗,我家也不例外,每年初冬母亲都会腌很多咸菜。腌菜的时节是舒心和快乐的。有了腌菜,家家冬季的饭桌就不会发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里有十来户人家,每到这时,母亲总会精打细算地找邻居婶婶阿姨们商量着一起去市场买菜来腌制。因为菜买的多可以给个批发价,比单独买要节省个块儿八毛。
腌菜的主角是箭杆白,这种白菜在我们家乡做腌菜最普遍。七、八根四五十公分高的长杆顶着几片手掌大的绿叶,杆长叶少,腌制好以后吃着爽口。当然,最好吃的腌菜要数萝卜干,它也是腌菜的生力军,吃起来柔韧爽脆,细嚼起来还丝丝甘甜。母亲和大妈大婶们选一个清晨,一次能买好几架子车的白菜和萝卜,前拽后推帮着农民,一路兴致高昂拉进了大院,然后七手八脚卸在了大院中央。过完秤,各家当家的和孩子们也兴高采烈地跑来帮忙分菜,彼时大院一片乐乐淘淘!
分完后,家家趁着艳阳高照,就先后开始了腌菜的工作。首先将家里的菜缸、菜坛搬出刷洗干净,摆在自家门口或廊檐下晾干。然后开始择菜,挑选出可供腌制的菜,接下来该洗菜了,洗菜的工作量要大些,往往三、四遍才能洗尽。洗干净后垛在长条凳或者搬出自家的大方桌上控控水,控完水后,搭在大院的晾衣绳上晾干,就可以腌制了。萝卜削头去尾洗净直接撂进竹篮里,等待切丝切丁用盐腌后用容易挪动的长条凳架起的竹箔、凉席追着日脚晾晒,也或者一刨两半盐腌后用纳鞋底的底线穿起,串成串挂在房檐下慢慢晒干。母亲总爱和邻居大妈大婶们一起在大院中做腌菜,一边劳动一边拉着家常交流着腌菜的经验,时不时还会互相开个玩笑,大院上空洋溢着欢快愉悦的气氛。母亲手脚麻利,做完或腾出手后总爱帮人洗个白菜切个萝卜,也或者指导一下缺乏经验的左邻右舍来腌菜。我们孩子们也爱跟前凑热闹,穿梭来穿梭去,尤其是萝卜上场时,有时虽也能中个小用跑跑腿递个东西,不过大多是为了能挣得几块青萝卜吃,经霜的萝卜爽脆甘甜赛水果。
那时我家人口多,日子艰
辛,母亲总要多下力气比别的人家多腌些,足足一大缸白菜和几坛萝卜干,有时还要另外加腌些萝卜樱和腊菜。母亲将洗净晾干的白菜均匀码在大缸里,码一层洒一层盐,一直码到缸沿,再用一块干净的大石头压在上面,将缸挪在阴凉干爽的地方盖好就算大功告成。白菜在盐的腌渍和石头的重压下,一天天收缩吐水,直到浸出的咸汁淹没石头。经过大概一个月时间的腌渍,咸白菜就可以食用了。腌渍好的咸白菜,色泽酱黄,鲜亮莹润,洗好切碎用红色干辣椒炝锅炒熟,吃起来咸香舒爽,是喝粥和下面饭的好佐菜。冬天,母亲隔几天就会炒一小盆,吃时,还不忘叮嘱我们兄弟姐妹要细细地吃,因为家里人口多日子更得细水长流。每到冬季家里总能闻到腌菜的咸香,一直会持续到第二年春天各种蔬菜大下市时。
我最爱吃母亲腌渍的萝卜干。母亲先将晒干的萝卜干用温水洗净,再装进坛子里,这个过程叫发菜,直到萝卜干吸足水份完全伸展恢复弹性。发时要洒些温水,水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发软没弹性,少了干硬,口味都不佳。母亲发的萝卜干恰到好处,配上焯过水的青丝芹菜,再切些干红辣椒、黄姜丁,吃时从坛子里抓出,淋几滴小磨香油,浇些香醋凉拌,色、香、味俱全,嚼起来嘎嘣脆。回回早晚有母亲调制的萝卜干,都能让我多喝两碗粥。
当兵复员后,我分在了一个离城四五十里远的乡下工作。工作忙回城少,母亲常惦记我乡下单位食堂的伙食单调乏味,年年冬天她都会腌些咸菜,在我临行的行李里回回都装几瓶让我带着调剂一下胃口。回到单位,有同事尝到母亲的咸菜,赞不绝口,再后来其他同事也知道后总是一抢而光。
母亲的腌菜,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直到我成家有了孩子单过后,母亲头上的青丝也换成了白发,挺拔的身姿也渐渐佝偻。那时,人们的生活早已有了很大改善,已经很少人家冬季再腌咸菜了,可母亲每年总是不厌其烦为我腌一些,因为她知道她的儿子最爱吃她腌的咸菜。我的生活里总能尝到母亲腌菜的咸香,总能承受到母亲无尽的爱,也总能让我找回童年的味道。
自从母亲去世后,直到现在的几年里,我已经很少再吃腌菜了。不是吃不到,其实超市和商店腌菜琳琅满目,品种齐全,比我母亲做的不知丰富多少倍,且不分四季唾手可得,可我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腌制的咸菜了。再也不能沐浴到母爱的光辉了,再也找不回童年的咸香了,我总怀念母亲腌制的咸菜,因为那是深藏在记忆里刻在生命中母爱的味道,即使是世上最美的山珍海味也无法替代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