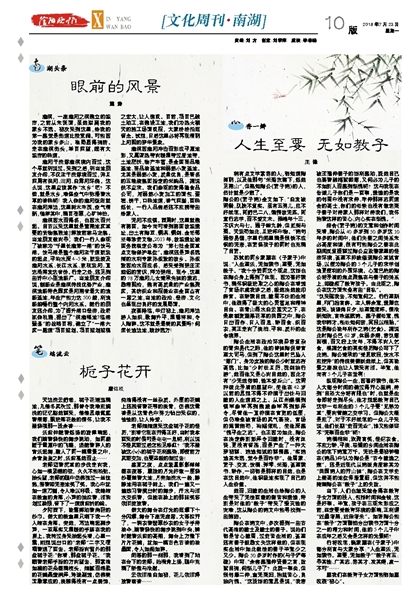王锋
稍有点文学素养的人,都知道陶渊明,以及他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熟知陶公《责子诗》的人,估计就是少数了。
陶公的《责子诗》全文如下:“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句通俗易懂,字里行间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责怪孩子的同时也充满了自责。
苏轼的同乡家颐在《子家子》中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我十分赞同这个观点,这话也在陶公身上得到了体现。因为喜好读书,满怀积极进取之心的陶公在看透了官场尔虞我诈之后,毅然决然挂印辞官。在耕读自适、隐居不仕的生活中,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灵富足和精神自由。在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之下,在桑麻稻麦蔬果花草的田园之中,陶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织而衣,真正走向了淡泊、平和、质朴的生命境界。
陶公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但到了陶公这里时已坠入“寒门”。身为庶族的陶公少时就志存高远,比如“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然而他又是心向自然的,因此才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使他在42岁以前的思想不得不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之上。从江州祭酒到镇军参军再到建威参军再到彭泽令,尽管他一直徘徊在官吏的低层,但仍难免被官场的风气裹挟。官场的蝇营狗苟,构陷倾轧,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也正因为如此,陶公在决定辞别彭泽令归隐时,没有沮丧,更没有留恋,而是产生了一种大梦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居家、责子、交友、饮酒、弹琴、采菊,甚至读书、耕作,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也是在这自然中,他积极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而,归隐的生活也给陶公的人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痛苦和遗憾,特别是对他的“教子”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从陶公的诗文中能寻找到一些踪迹。
陶公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一些古代高洁的隐士及隐士的妻子。说她们都是甘心隐居,过贫苦生活的,甚至还有妻子鼓励丈夫这样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此做法的妻子毕竟少之又少。陶公50多岁时作的《与子俨等疏》中写:“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了?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常被王孺仲妻子的话所感动,既然自己也裹着破棉絮御寒,又何必为儿子的不如别人而感到惭愧呢?这与我现在告诫儿子你们是一回事,遗憾的是我的邻居中没有求仲、羊仲那样志同道合的高士,你们的母亲也没有像老莱子妻子对待家人那样对待我们,我怀抱着这样的苦心,内心实在惭愧。”
结合《责子诗》的文意和创作时间来看,陶公从40多岁到50多岁这10年多的时间中,他们夫妻之间关系未必高度和谐,很有可能陶公之妻在此期间反复提醒过陶公应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甚至不排除催逼陶公重返官场,以便为陶公的5个儿子的求学创造更便利的外围环境。心意已绝的陶公将矛盾的焦点聚集在与妻子的关系上,却疏忽了教育孩子。由此观之,陶公在这方面未免有些“自私”。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是陶公晚年所作之诗《乞食》。据说此时陶公已62岁,体弱多病,常饥寒困顿,而又赶上灾年,不得不向人乞食,根据乞食的真实经历陶公写下了此诗。陶公秉承的“受恩欲报,饮水不忘挖井”的传统美德跃然纸上,但其晚景之凄凉也让人读来有泪。毕竟,他尚有5个儿子在世啊!
纵观陶公一生,因喜好读书,他本人大部分时间的确过得开心滋润,待到“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时,也就是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才想起教育自己这非一母所生的5个儿子要“兄弟为重”,要向管鲍之交学习。但陶公大概是忘了,对于不好纸笔的一众儿子来说,他们长期“贫而无业”,谁又能保证不“无事而生非”呢?
诗酒相和,欢聚言笑,经纪衣食,不忘力耕,平淡、枯燥的乡间生活在陶公的笔下诗意万千。无论是最初钟嵘在《诗品》中认为陶公是“古今隐逸之宗”,还是近现代从诗派角度称其为“田园诗人的开山祖”,陶公在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毋庸置疑,但这并不能掩盖陶公在“教子”上的失败。
当下,人们也越来越舍得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投入,包括时间和金钱,这是好事。毕竟,孩子在三观未形成之前,注定要受教育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墨者黑,近赤者朱”。如若陶公能在“教子”方面哪怕分出读书方面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他的5个儿子中在成年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行将收笔,摘家颐在《子家子》中部分所言与大家分享:“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攻其病,废一不可”……
愿我们在教育子女方面能都如愿收获“初心”。
温馨提示
本页面内容不允许直接阅读,请通过《信阳日报》客户端浏览查看。

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