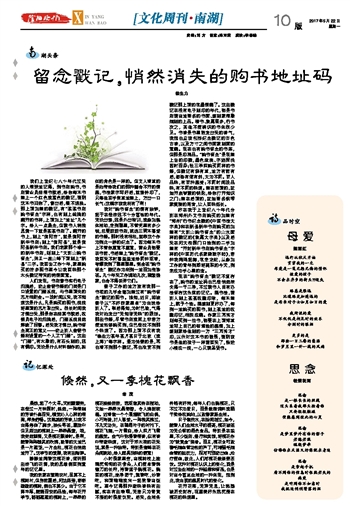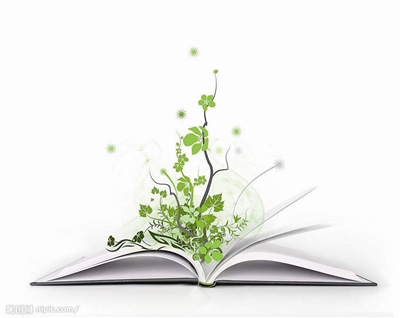 |
徐生力
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来的人清楚地记得,到书店购书,书店营业员结清书款后,给你每本书盖上一个红色或蓝色的戳记,表明这本书归你了,售出后,概不退换。那上面加盖的戳记,有“某某书店购书留念”字样,也有刻上线描的翻开的书样,上面加上“地址”几个字。给人一点悬念,但读书人稍微思索一下就是某某书店了。翻开的书上,刻上“信阳市”,就是信阳市新华书店;刻上“信阳县”,就是信阳县新华书店。我们老家那个唯一的新华书店,则刻上“大别山购书留念”,并且一座山峰下面刻上“新县”二字。我回去工作十年,家里购买的许多图书至今让我回味那个木头戳记带来的诗情画意。
人们发现,书店售书实行电子扫描后,防止偷窃书籍的门岗是门口设置的门禁系统,与书里面夹的芯片相配合。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凡是购买的图书,统统将里面的芯片取出来。很长时间我才悟出来,那是你在结算书款后,收银员电子枪扫描后,门禁系统自然解除了报警。后来我才悟出,购书留念真正的意义——防止别人偷窃书籍所设置的一个人工“门禁”。这些“门禁”,有木雕的,有石头刻的,还有铜印。无论是什么材料制作的,担任的角色是一样的。但文人看重的是她带给我们的那种割舍不开的情感,书法家字写好后,就差钤印了,只等他双手慎重地盖上,方出一口长气:这幅字该我所有了啊!
我对“购书留念”的情有独钟,起于在经济还不十分富裕的年代。无论出差,还是外出培训,或参加集体活动,走到哪里,不管兜里有多少钱,总要逛逛书店,挑选三两本喜爱的书籍。那时没有相机,就靠这个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了。因为每本书上不管你原意不愿意,营业员都要在书前、书后盖上“购书留念”戳记。我回来不时喜滋滋地给同伴观看,夸耀我到了哪里哪里。完全视“购书留念”戳记作为所到一地而加倍珍视。几十年来工作调动几次,频繁搬家,也舍不得丢弃它们。
妻子工作的地方放有我那一书柜的几乎全部加盖过有“购书留念”戳记的图书。谁知,近日,却被妻子以“不好往家里拿”为由送给别人了。事后得知,为时已晚,气得我对她发出“无知者无味”的狠话。那些书籍,尽管书店或网上非常方便地能够购买到,但已经找不到那个味道了。因为那上面不仅有我“徐生力某年某月某日于北京(或上海)”等字样。最为关键的是,再也看不到那个戳记,再也欣赏不到戳记那上面的笔墨情趣了。这些戳记在没有电子刻印的年代,都是书店请当地著名的书画、篆刻家精雕细刻的上品。楷书、隶属居多,行书次之,其他不便辨识的书体很少见。书香是书里散发出来的香气,我想也应该包括纪念戳记的古色古香,以及方寸之间书画家刻画的意趣。现在也有购书留念的书签,但那是印刷品。“购书留念”是现盖上去的印戳,墨色浓淡、字迹深浅因时而异;张三李四购买同样的书籍,但戳记有轻有重,地方有前有后,姿势有倾有斜,大为不同。百人品味,有百种感受;不同时间段品味,有不同的味道。盖在前面的,犹如开启智慧的钥匙,给你打开知识之门;盖在后面的,犹如著名钢琴家演奏的尾音,让人回味悠长。
好在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别在郑州外文书店购买的加盖有“郑州”行书纪念戳的《中国书法大字典》和在新县新华书店购买的加盖有“大别山购书留念”的山水画样的戳记的《隶属大字典》以及后来在河大校园门口拾到的二手加盖有“开封新华书店购书留念”字样的《中国历代名家楹联字帖》,常伴我闻鸡起舞,笔走龙蛇,从参加工作的青年到即将离职的今天,到老成为手心里的宝。
现在“购书留念”戳记不复存在了,购书的地址码也已经悄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不过读书人自有办法留存这永恒的记忆。搞书法,请别人刻上某某收藏印章,每本盖上,赋予个性。搞篆刻更好办了,每到一地购买的图书,刻上某地的收藏印记,相映成趣。作家三耳秀才则每买到一批书,都要在上面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哲理性的感悟,加上篆刻家给他刻的一方“三耳秀才”印,以示对这本书的敬畏,表明该书是他的孩子一样请回来了,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只读圣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