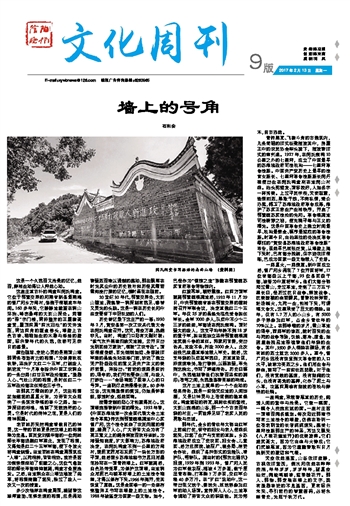|
| 闵氏祠堂书写标语的南面山墙(资料图) |
石和安
这是一个久远而又沧桑的记忆,然而,鲜活生动得让人怦然心动。
这座庄重古朴的祠堂叫闵氏祠堂。它位于鄂豫交界的河南省新县最南端的箭厂河乡方湾村,修建于清朝咸丰年间。160多年来,它静静地隐匿在群山环抱、峰峦叠嶂的大别山深处。肃穆的“吞”字门楼,两排整齐的正屋檐高堂宽,屋顶四周“四水归池”的天井造型,两边四角的鳌鱼兽头,墙壁上古色古香、栩栩如生的木雕与彩绘的壁画,昭示着年代的久远,依稀可见往日的盛景。
撞击眼球、走进心灵的是南面山墙那两条苍劲有力的标语:“为保障秋收秋耕,坚决扩大红二十五军,打破敌人新进攻”“十月革命指示中国工农群众的一条出路!红廿五军政治部宣。”激励人心、气壮山河的标语,是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手书。
在那风刀霜剑的岁月,这些标语犹如燃起的星星火苗,为劳苦大众照亮了一条谋求幸福的奋斗之路。如一声深切的呼唤,唤醒了无数迷茫的心灵。它是时代的传神之笔,更是人们的精神图腾。
老百姓历来把祠堂看做自己的神灵,这一带的百姓更是把这墙上的标语奉为圭臬。国民党刘镇华部的一位闵姓师长率部追剿红军至此,发现了标语,又得知是红二十五军军部,便下令放火将祠堂烧毁。当地百姓在祠堂周围筑成“人墙”,以死相拼,苦苦相劝。或许是因为宗亲情结动了恻隐之心,这位气急败坏的师长率部悻悻撤离,祠堂才免遭涂炭。之后,当地群众在山墙边堆放了柴草,将标语掩藏了起来,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查。
多少次徜徉在祠堂周围,凝望着这雄浑遒劲、笔锋老道的标语,总是涌动着强烈而难以遏制的感动,那些飘落在时光风尘中的历史散叶和历经风霜雨雪淘洗打磨的记忆,顿时呈现在眼前。
20世纪30年代,鄂豫交界处,大别山腹地,聚集着一群深刻有远见、睿智又灵光的头脑。这是一群在历史长河中注定要留下华丽轨迹的人们。
历史曾记录下这庄严的一幕:1930年2月,黄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闵氏祠堂召开。这天,晴空万里,热闹非凡。当时,祠堂门口贴有大副对联:“紫气东升黑暗扫除天地撼,云开日出光明团结万家欢”,横联“工农专政”。面容清瘦俊朗、目光炯炯如炬、身穿破旧军装的吴焕先站在彩门前,讲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意义及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并指出:“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艰辛的,我们可能要住山洞,与敌人打游击……”会场响起了振奋人心的口号声。一盏明灯点亮漫漫长夜。80多年过去,这充满激情的演说,仍如晨钟暮鼓,穿透时空,悠然回响。
按需定制的贴心才能赢得民心。这面墙连接着新中国的曙光。1932年春,《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传达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心区箭厂河,这个法令抓住了农民问题的精髓,凝聚了人心,广大劳苦大众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而欢呼雀跃。为增强知晓度,扩大影响力,苏维埃政府决定,在闵氏祠堂不到一公里的方湾村,请泥瓦匠用石灰泥了一块长方形的平面,然后请乡苏维埃秘书方思归用墨笔抄写在一面青砖墙上。红军撤离后,白色恐怖笼罩,为保护这面墙,当地群众用泥巴与稻草将墙上的土地法令糊盖,才得以保存下来。1966年揭开,使其恢复了原貌。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处保存完整并且书写在墙壁上的土地法令。1988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已经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内。
红旗再举,朝野震惊。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鄂豫交界的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年仅25岁的吴焕先临危受命担任军长。全军7000多人,队伍中不少十二三岁的娃娃,军部设在闵氏宗祠。面对强大的敌人,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童子军,担当起独立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重任。郭家河首捷,突出奇兵,攻敌不备,歼敌2000余人。此次战役已浓墨重彩地载入军史。随后,这支年轻的队伍孤军远征,历重重险阻,排道道难关,敢打善拼,以弱胜强,率先到达陕北,书写了辉煌传奇。历史征程中,永远铭刻着他们执着而坚实的脚印;苍穹之间,永远激荡着英雄的呐喊。
这片土地上演绎的一个个生动的经典传奇,既是一曲恸天泣地的人间话剧,又是让神灵与上苍倾倒的隆重祭仪。祠堂斑驳的砖瓦,枫树壮实的繁枝,大别山连绵的山谷,那一个个古老而年轻的村庄,一同诠释见证了老区人民的勇敢与忠诚。
那年代,全乡的青壮年大都当红军上前线打仗,留守的妇女与老人便组织起来,扛起了生产与支前的重担。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后方总医院、被服厂、税务局、消费合作社,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运输队、看护队、帮耕队。据当时的《鄂东北通讯》报道,1929年到1933年,箭厂河人民为红军做衣服、棉被4万多套,做千层底青布鞋、打草鞋7万多双,交红军公粮40多万斤。在“扩红”运动中,这一带出现父送子、妻送夫、姐送弟参加红军的动人场面。宣传深入人心,土地革命调动了劳苦大众的积极性。民为邦本,自古亦然。
青砖黑瓦、飞檐斗角的古建筑内,几条简陋的旧式板凳摆放其中,房屋正中的农民协会犁头旗下,摆放着旧式的审判桌。1927年,在闵氏宗祠10公里之外的七里坪,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府司法机构——七里坪革命法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法官女庭长、七里坪革命法庭庭长闵丹桂便出生在闵氏祠堂所在地闵山村组。她头剪短发、面容姣好,人如名字一样秀美。上过平民学校,天资聪慧,性情刚烈,果敢干练,不徇私情,秉公办案,捍卫了苏维埃政府革命成果,维护了苏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开启了鄂豫皖苏区法治的先河。革命根据地司法萌芽之初,便充满平等与正义的曙光。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建立时间最早、机构最健全、程序最规范的革命法庭。时至今日,由她签批的处决反革命罪犯的“黄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虽然早已纸张泛黄,从墙壁上揭下来时,已有部分残破,但字迹依旧清晰,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载入了史册。
一路星火,一路燎原。新中国成立后,箭厂河乡涌现了7位开国将军,17位省部级以上干部,93位县团级干部,被誉为中原将军乡。他们大部分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血雨腥风,冒着枪林弹雨,赴汤蹈火,九死一生,能活下来,可谓福大命大。这里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当年,仅有1.7万人的小山乡,有5000多子弟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的70%以上。在那峥嵘的岁月,雪山草地的艰辛,西路军的惨烈,随时而来的生与死的战争考验,饥饿、寒冷、疲惫,如恶魔般残忍地吞噬着他们年轻的生命。其中,3500多人牺牲在疆场,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000多人。至今,箭厂河乡还没有恢复到大革命前的人口水平,被称为英烈之乡。他们用生命与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悲歌。对于他们,没有宽敞的墓道,没有挺阔的坟头,也没有高耸的墓碑,化作了泥土与小草,坟墓四周唯有挺拔的苍松与鲜艳的杜鹃。
一座祠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阅透人间的繁华与沧桑。它像一幅画,一幅令人流连忘返的画。一座村庄因一面墙而闻名遐迩。每次贴近那堵书写有土地法令的墙壁,仿佛在聆听一位苍老明世的长者娓娓道来。感受七里坪法庭那庄严的神圣,耳边又飘来《八月桂花遍地开》的优美旋律。它们威武高大,因为它由血与火铸成;它们沉雄厚重,因为它蕴藏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和气概。
天空依然湛蓝,山谷依旧寂静,古枫依旧繁茂,倒水河依然在哗哗流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望星空灿烂,闻蛙鸣稻香,迎春暖花开。那人、那物、那定格在墙上的文字,既有激励奋进的不息基因,更有昭示未来、导引前行的智慧密码,必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