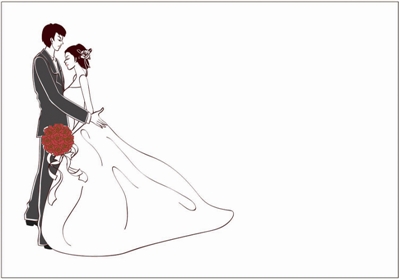 |
艾虹
在欲望都市的电影结局里,那个穿着薇薇安韦斯特伍德订制婚纱的文艺女王,并没有艳光四射的踏入红毯,因为她的夫君半路逃跑了。
那些害怕婚礼甚至厌烦那一切婚礼习俗的人,无法接受如玩具木偶一般的被摆弄,无法接受两个人的感情非要和不相干的那些人纠缠在一起。而我,曾经也以为,我不需要一场婚礼,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折腾一场给别人看的宴席。
可是,现在我却坚定的认为,在走入婚姻之前,我们一定需要一场婚礼。
几年前,在张家界参加闺蜜的婚礼。我们一起住在酒店。第一天清早,化妆师来敲门,她穿西式白纱裙。她跟我说:“我们土家族嫁女儿,是伤心的事,所以不能大张旗鼓。所以我穿白婚纱,白色是为自己而穿。”当夜,按照土家族的规矩,所有娘家女眷围坐在一起唱歌。她坐在正中央。那些旧时的歌谣的已经没人会唱,于是,就唱大家都会唱的那些歌。没有KTV,拿手机放伴奏。
晚上,我们俩把那席纱裙工工整整铺在床上,她说:“给它照一张吧,虽然不是Verawang,却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穿上它。”第二天,更早的清晨,天还蒙蒙亮,红裙上身,金钗插满头。化好妆。一屋子的娘家亲眷。和爸爸妈妈合照,和外婆合照,和舅舅舅妈合照,和那些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人合照。
临近中午,听到楼下鞭炮齐鸣,听到乐器混杂在一起的热闹声响,当一行男眷涌上来,屋子里瞬间拥挤起来。各种喧闹中,她和妈妈相拥而哭,旁人都在劝,“眼妆要哭花了”“不要误了时辰”“这是喜事啊”,还是止不住哭成泪人的母女俩。后来,新娘子在簇拥下,走下楼梯,上了婚车。鞭炮再次齐鸣,人群浩浩荡荡的离去,奔赴一场真正的喧闹。
我记得闺蜜的父亲在台上是如何义正言辞地念完那张讲稿,每一字每一句里面都是两个字:托付。不管台下的人,是否听清,都不重要。那个一字一句写下,再一字一句念出来,这个交织着托付的过程,对他来说,最重要。她说:“这一生活到现在,第一次听到她内敛的父亲,在这么多人面前如此这样高调地赞扬自己的女儿。”
我结婚的时候,我妈是没有哭的。她大概忙碌的没有时间,我预计她也不会哭。我只记得那天中午的鹅毛大雪。记得一张张闪过的熟悉又陌生的脸庞。记得婚礼上他说:婚姻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说得振振有词。记得楼下交杯碰展,我们在上面对唱: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是从我的婚礼的那一刻后,意识到,仪式感对于人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盛大的欢聚,盛大的离别,盛大的狂欢,盛大的合唱,盛大的礼物,才足以成就人生的丰富。
我是从闺蜜的婚姻里,感知到,仪式感对于人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内心终究是需要戏剧感才能完整的。不管幸福还是悲伤,再普通的日子,你也是你的女主角,需要在某些时候,金钗当头,号啕大哭。
你穿红裙,你着盛装,你们交换戒指,你们举杯喝尽杯中酒,在那场盛大之后,以后幸福或是不幸福,都要你自己一个人走了。你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好好地跟过去的自己离别,好好的听到父母说出的托付,好好的感受到众人的见证。你知道,此后的人生,确实已与过往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