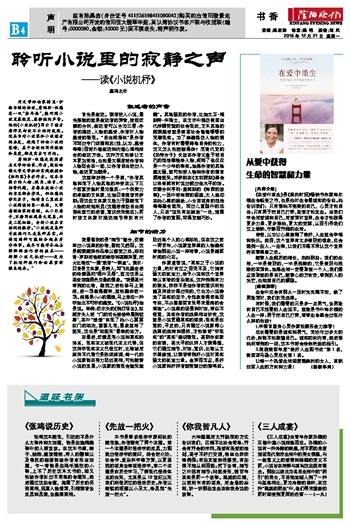|
鹿鸣之什
用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话说,詹姆斯·伍德有一双“金耳朵”,能听到小说里最轻灵、最静谧的声音。他的《小说机杼》写出了读者看得见却说不出的好发现。这本书对小说家和小说读者的启发,超越了评论小说的范畴,其中分析的写作经验和角度,都是实在可用的。
詹姆斯·伍德是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者,现任哈佛大学文学批评实践教授和《纽约客》专栏作者。这本书提出的人物、视角、语言、对话等问题,在每本谈论小说的书里都会涉及,但伍德的妙处在于,他将自己置放在小说阅读的第一现场,又带着理论家的清醒,从小处着手,不涂写粗线条大笔墨,而是工笔细描,分析小说在言语间的微妙。“小说既是某种奇技淫巧又是某种真实,而将这两种可能结合起来并非难事。我尽可能详尽地去解释那些巧妙的技术——拆解小说之机杼——是为了把这种技巧和世界重新联系起来。”
叙述者的声音
这就牵涉到一个矛盾,“作者风格和笔下人物风格的冲突在以下三个因素齐集时最为激烈:一个很卖力的卓越的文体家,比如贝娄或者乔伊斯;而这位文体家又致力于跟随笔下人物的所知所思(这通常借助自由间接体或它的后裔,意识流来完成);同时该文体家对描述细节特别有兴趣”。风格强烈的作者,比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文字中模仿美国当代浮躁荒诞的社会现状,文本风格的阅读感受就是美国社会嗡嗡嘤嘤的无聊现实。为了准确模仿人物的语体,作者有时需要降格自身的能力,这又怎么能控制得住?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失败在作者太急于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人物,忽略了他仅仅是一个少年的事实。如果作者的风格感太强,就可能将人物和作者的语言混淆起来。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会让布鲁姆有时说出超出他水平的话。伍德分析亨利·詹姆斯的《梅西的故事》,一段中将梅西的疑惑、大人烙印在她心里的尴尬、小女孩视角的想法等等融合起来,写出儿童眼中的成人,只在“说来有些尴尬”一处,透露了作者的意图,写得克制巧妙。
细节的活力
我最喜欢的是“细节”部分,伍德举出小说里的妙喻,熨帖又舒服。这是阅读翻译作品难以察觉之处。菲利普·罗斯将性欲的粗俗和高雅并置,把火比喻成“一撮”或者“一群鱼”。索尔·贝娄是文体家,是诗人,写飞机腾空后的哈德逊河“绿中见绿”,因为这是从高空俯瞰绿色交叠的景象。“我最高兴看到的比喻,疏远之后能够马上联结,后一项做得漂亮,就能藏住前一项。结果是小小的震惊,马上变成一种非如此不可非的感觉。”《小说机杼》如是说。举例: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拉姆齐夫人将“门的舌头缓缓伸展到锁里”,其中“缓缓”体现了她小心翼翼拉门的动态,寥寥几笔,景象就活了起来,这也是“动起来”最难的地方。
在最后,伍德思考小说和真实的关系,现实主义被现代主义代替,但这并非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比喻被用滥并不代表它是陈词滥调,每一代的小说家都在努力贴近真相,可能随着小说的发展,小说家的表现会越来越贴近单个人的心理动机,但在这之前一两百年,小说家世界里的人物确实曾如那些小说一样活着,小说是凝固时间的化石。
作家唐诺说,“真实之于小说的力量,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拥有强大的抓地力,给予小说和这个世界难以言喻的复杂联系,这种饱满有力的联系,往往不是创作者的意识所能遍及并设计得出来的,它也为小说铸造了坚实的底子,令想象变得简单而专注,不必屡屡回首来寻求最终的合理性”。小说里的场景和对话,看似不经意,其实作者的选择相当讲究,这就是小说贯通真实的渠道:现实是任意的,平质的,只有通过小说家精心选择的浓缩和提炼,才能够将“非现实”的“真实”确切表现。高明作曲家的曲谱,高水平的乐评人才读得懂,它们通过细节、对话、意识、比喻从文字里渗透,让读者看到好小说对真实强大的抓地力量。金声而玉应,是好小说家和好评者默契谱出的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