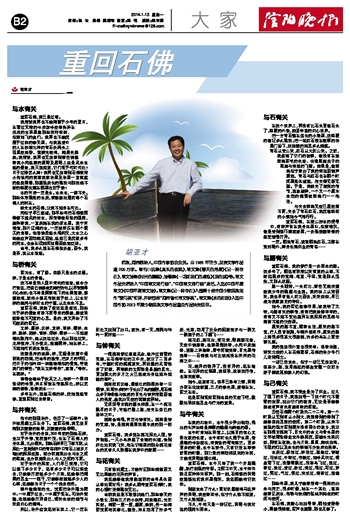胡亚才
与水有关
重回石佛,我已是过客。
我清楚我再也不能陶醉于少年的夏日,在雨过天晴的午后赤手空拳疾奔在浅浅的水田里逮那些欢呼雀跃、似箭如飞的鱼们;我再也不能沉浸于过往的春天里,与我恋爱中的人在妙塘北岸的青石条码头上观星空浩渺,读萤光蛙鸣,闻晨色寡淡;我清楚,我再也无法看到曾经诱惑着我小河纵横的原野及原野上总是风生水起的景象,我只想知道,它们现于何时何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再也无法看到石佛镇南小街临河的院落我家老屋及老屋一直氤氲的袅袅温馨,那源远流长的柔软与那连绵不断的坚硬收藏在哪里收归于谁?
水的背后一定是水。水生水,一滴不失。那些体形柔美的水流,曾脉脉地通向每个石佛人的所在。
缺失水的石佛,让我不知身在何处。
河似乎早已逃遁。那早些年把石佛镇围得密不透风的活水,深情得像母亲的眼睛,滋养着我,一直流淌在我的泪水里。我宁肯相信,那片辽阔的水,一定被挤压在哪个逼仄的角落。倘若谁昂起头颅问天,大水之心终能应声而动闻风而起,纵然已是沉寂多年的死水,也会在顷刻间汹涌而恣意泛滥。
当年,我多么想在石佛做条鱼,而今,我是否,该从水做起。
与桥有关
因为水,有了船。但船只是水的点缀。桥,才是水的骨骼。
这不单是诗人眼中简约的意象,适合分行表达,把自己铺排成怎样的诗句,以尽情演绎内心生活;也不单是画家笔下的水墨素描,寥寥数笔,就将小镇风情跃然于纸上,以水对桥的滋润与桥对水的守望,从此生生不息。
重回石佛,我除了叙述还是叙述,那些关于桥的景象有着不同寻常的温暖,抑或承载着秘不可宣的心思。是的,我又开始了不可救药的回忆。
文桥、漂桥、云桥、龙桥、草桥、霸桥、生桥、燕桥、荷桥、官桥、师桥、雪桥……不知疲倦地陈列中,她从这边过去,他从那边过来,此岸彼岸,不分彼此,模糊两岸,站在桥上,不知如何向流水表达。
连接是岸的选择,桥,无疑是连接中最明亮的动词,把当年的激情,把岁月的喟叹,把日子的低吟和一株植物相似的便笺,带进我们的曾经:“我在文桥等你”,或者,“等你,在荷桥。”
谁都会端坐于秋风之上,给桥一个温和亲切的手语,并且留意在情感深处,桥以怎样的姿势,亲吻流水……
多年在外,想起石佛的桥,犹如想起青春,直想回到过去看看。
与井有关
街中的那眼老井,经历了一场事件:老井被混凝土压在身下。重回石佛,我无法目睹那灰蒙蒙的耻辱,灰蒙蒙的耻辱啊。
对于老井的身世,300年前的那块石碑,先立于井旁,竟枝繁叶茂,长在了石佛人的身体里,扎出根来。那块石碑早已下落不明,从深处一直爬到井口的青苔和井口青石上被岁月勒出的深深纹路,却分明测量出水与水之间的距离,也分明测量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对于老井的深度,人们早已摸清,它可以装下多少日子,还有多少日子可以装进去,它能够打捞起多少个月亮,还能够把潮湿的思念一一晾干,它能够救援起多少人的心事,还能够为日子一个个洗去伤疤。
事件像幽暗的光,试图把老井隔为两半:一半属于过去,一半属于现在。可老井完整,依然能够打开自己,倾听生活的细节与来自内心的轰鸣。
所以,老井应该还活在世上,它一定在别处又找到了出口。或许,有一天,清冽与呻吟一同浮起……
与钟有关
一棵槐树穿过滚滚风尘,像冲过箭雨的英雄,在石佛学校的正中央,挺立了二百多年,守望时间的娓娓道来,再狂暴的风雨都有了归宿,再毒辣的太阳都是昌盛的恩光,更加强大的岁月之火已然成为身边知冷知暖的落叶。
槐树枝向云端,最健壮的那根拎着一口铜钟,四周许多的叶子长出了鸟的翅膀,用石佛众多子弟骨感与铁质的目光与钟声清脆而催人的亮度,垒筑出天空的窝抑或驿站。
无须探寻古槐的源头和根,在一个槐花飘尽的日子,背起行囊上路,消失在自己的森林之中。
槐树会鸣唱,肯定与钟有关。槐树是钟的支撑,钟,是槐树最温软最本质的那一部分。
重回石佛,我多想在槐花深处入眠,钟声响起,一只小鸟挣脱了食物的纠缠,恰到好处地向我飞来,衔在它嘴里的那朵槐花洁白的乳香久久弥漫在我梦中的家园……
与花有关
只有亲近泥土,才能听见那些细微而又无比温暖的花开的声音。
我还能够像我清澈透明的当年具体而从容地面对吗?我多么期待重回石佛时,我的心顿时变得柔软无比。
当初我总是不敢惊扰她们,那些春天的小美女,那些三月的小妖精,姹紫嫣红,光芒四射。绚丽一层一层,凝固,堆积,另一些绚丽试图将其溶化,搬走,并且动用了许多气流、光束,动用了云朵的闲庭信步与一群又一群燕子的上下翻飞……
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野蒺藜花紫,天空中铺排着,池塘里倒映着,小河中流淌着,道路上奔跑着,眉宇间微笑着,目光里传递着……石佛镇与村庄被淹没在茫茫的花海之中……
花,能开的都开了,没有开的,还在继续。在花开的过程里,我坦承,我喜欢抒情,也喜欢叙事。
如今,总算有花。但早已势单力薄,田野分明在收拢欲望,三月的春色里,疲倦在左,困乏在右。
还是回到现实回到各自的天空下吧,默默地承担起思念与行为的重量。
与牛有关
在我的印象中,水牛很少弄出响动,偶尔的叫声始终是浑厚的黝黑与鲜嫩的绿。
水牛时常站在田埂上,以满目的信心丈量收获的长度。水牛有时长久浸于水里,借晨曦的手指梳妆,倚黄昏的臂弯解乏。更多更多的时候,水牛在耕作,只有它走在犁铧前面的时候,那力量的律动和肌肉的本真,才能使田野波澜壮阔。
重回石佛,水牛只给了我一个步履蹒跚,渐行渐远的背影。太阳正中天,水牛并未驻足回眸并未留声。那一刻,石佛镇的田野空荡荡地向我怀里倒来,我还哪能将它扶住。
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机器轰鸣马达声声的田野,我空着双手,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又什么都知道。
不久,牛将只是一种记忆,田野与我对视的眼睛叫陌生。
与石有关
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石头更像石头了,坚硬的外表,抱紧丰富的内心世界。
把一方青石镶在悠长的小巷里,这坚硬的徽记多么柔软;把一帧红石嵌在敦厚的老屋门垛下,这粗糙的构思多么细腻。
青石从安山来,红石从大别山来。之前,我忽略了它们的故事,像没有在意斑鸠羽毛的色彩、尖喙距离虫子的距离与突然的飞翔。结果是,像斑鸠似乎看出了我的短视而销声匿迹,青石与红石也在哪个时间里集体遁逃,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我缺失了触摸的情节,想象破碎,一个又一个原本生动的词语被斑鸠们一一衔走。
与失去斑鸠天空已显空洞不同,失去了青石红石,我沉稳坚实的小镇如今气喘吁吁。
重回石佛,在跋山涉水的搜寻中,有种声音在我身体里叫,似曾相识,像是受到惊吓抑或委屈,一条裂缝随着痛的感觉缓慢打开。
一定。哪块青石,或者哪块红石,正蹲在荒郊野外,浑身长满怀念的青苔……
与路有关
重回石佛,我的穿行是一条陌生的路。这多年了,哪还有明清以来官道的从容,不断拓展后的宽阔、笔直、平坦,竟是那么迅疾,又那么迟疑。
路一头朝南,一头向北,曾经无数次撩拨我少年的眺望与念想。我的祖上从南而来,我也早有亲人向北而去,来来往往,早已成为我家族史的特征。
如今,我的回忆像堆苹果,被我啃了又啃,与路有关的事情,常常把我拴得牢牢的,常常又不知不觉地盛开在我深深的思绪与痛苦不堪的忧伤里。
原来的路不直,顺着水走,原来的路不宽,行人昂首挺胸,车辆井然有序,原来的路上树很多很高大很蓊郁,许多的鸟在上面安营扎寨。
我的想法很朴素也很简单:沿着老路,南来北往的人在石佛逗留,石佛的老少爷们儿走南闯北。
一切已经发生,似乎一切已无法改变。但至少,路,该用绵延的姿态安慰一位归乡游子抑或孤独旅人的幻想。
与己有关
重回石佛,我不完全是为了怀念。过久了眼下的日子,我想找寻一下这个时代不需要的东西,找出它们的棱角,无论是否能够拼成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图案。
历经石佛两个时段共二十二年。第一个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想得到的得到了能够自由思索的空间。第二个时段,从并不遥远的远方回到根本没有异乡的故乡,我立在那棵古槐树下,目光中的含义与骨头里的文字被霜染得愈发冷静深沉,而额头光亮闪烁,即使在夜晚,也与月亮、星星、狗吠虫鸣、不眠的灯以及生长的事物不分先后地亮着。
水流过,船划过,桥走过,路跑过,钟敲过,花采过,牛牵过,书教过,如手风吹过,倾盆雨下过,没膝雪飘过,报喜鸟飞过,想过,看过,谈过,爱过,盼过,笑过,唱过,写过,梦过,哭过,气过,恨过,快乐过,痛苦过,遗憾过……
那些年里,我几乎能看清每一棵树的出生与死亡,很多时候,站在一个高处 ,甚至能看见流水、街巷与炊烟的弧线所构成的时间与空间。
在石佛,我耐心地找寻着,哪怕爱渺缈小,温暖很细微,回声也羸弱,那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