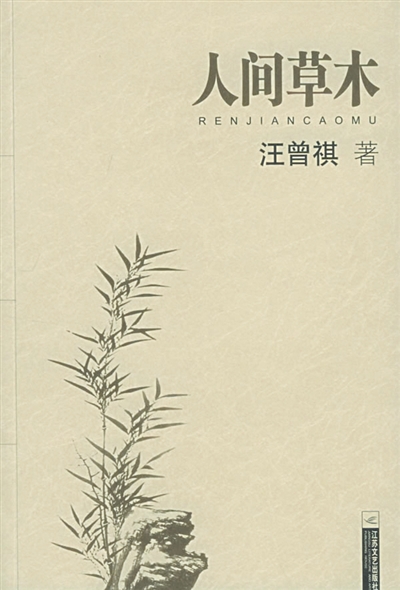 |
“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读完《人间草木》,越发感到哈姆雷特王子问的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对古代人或者宗教而言,活着是为了死去;活着和如何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去和如何死去。对死亡有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有了一种选择,死亡便不再是一个自然事件了,成为一种文化应对。对现代学者来讲,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经历过“祛魅化”的现代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认真、高贵地生活?
周宁所著的《人间草木》通过四组人物的死亡,反观其生命,正如书中说的“面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态度”。
从生命的起点来面对生命,是一个动物式的自然过程;从生命的终点来反观生命,则是人类的文化态度。为了死去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死去,不仅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同时也是宗教和非宗教的区别之一。
最近,耶鲁大学雪莱·卡根教授的死亡课程在网上受到追捧,卡根教授秉承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对待死亡的逻辑和科学传统,即围绕着肉体论和灵魂论(或二元论)而展开讨论。与西方对待死亡的理性态度不同,我们在对死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常常不关注来自大脑的理性和科学,只重视发自内心的关注和悟解。非此即彼的西方理性和彼此彼此的东方悟解,决定了东西方文化中对待死亡和生命的不同态度。
《人间草木》第一组人物马礼逊和伯格理都是传教士,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福音来到中国。然而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幸福吗?在这个问题上,马礼逊的绝望和伯格理的期望同样彻底,不过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两人作为上帝仆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宗教观念中,生死是对信仰的实践方式,死是有意义的,甚至是诱人的。书中的弘一法师视生如死,虽存犹殁,死亡不过是“去去就来”。哲学上的二元统一认识,决定了中国文化对待死亡和生命之间的圆融态度,所谓圣人贵一也。看看苏曼殊,一生都是游走在出家与住家、放纵与持戒、大爱与决绝、觅死与寻欢之间。
卡根的死亡课程仅仅是把死亡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科学认识,这种死亡放在动物和人类的身上没有区别。西方的死亡学说中,无论是肉体论还是灵魂论,都不能囊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死亡的态度:生即死,死亦生。生有何欢,死亦何憾?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宗教圣人毕竟是少数,芸芸众生依然逃脱不出生离死别的凡俗。
作者关注的前两组人物虽然都是宗教人物,但对死亡的认识,完全反映出东西文化的本质与区别;后两组人物都是非宗教人士,在他们充满个性的生命中却有着对死亡的共同认知:死亡不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文化的选择结果。
(据《中国青年报》)
